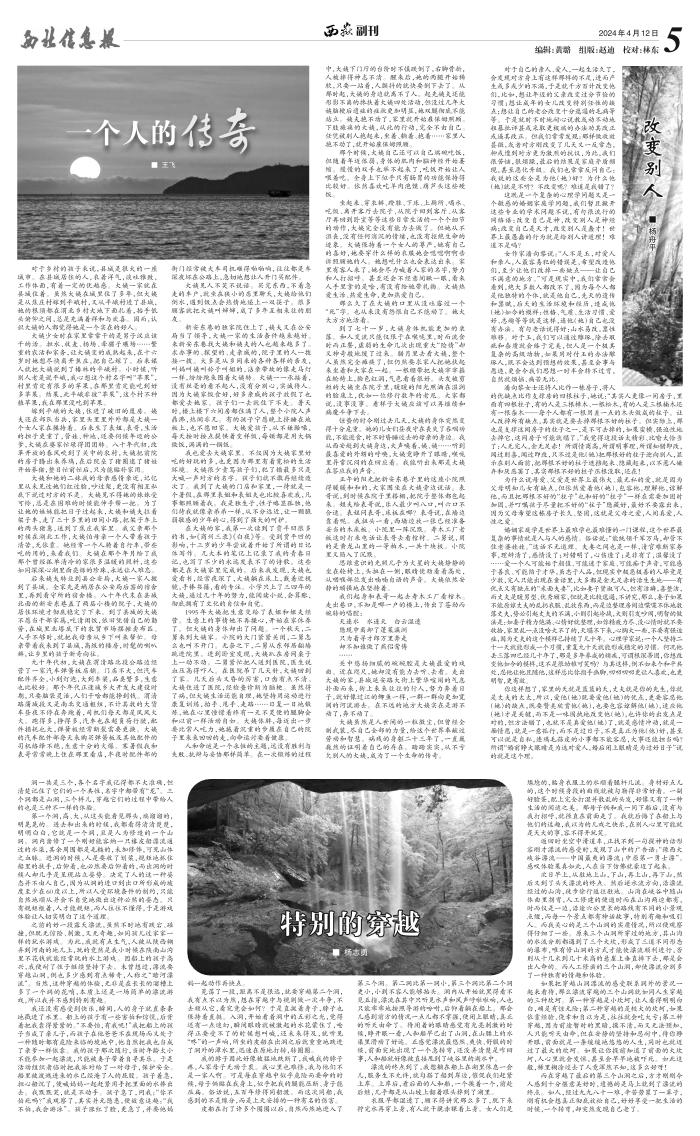一个人的传奇
文章字数:3,818
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,县城是很大的一座城市。在县城居住的人,衣着洋气,谈吐雅致,工作体面,有着一定的优越感。大姨一家就在县城住着。虽然大姨在城里住了多年,但大姨是从焦庄村嫁到平峨村,又从平峨村进了县城,她的根须都在渭北乡村大地下面扎着,抬手低头俯仰之间,总是充满着祥和与欢喜。因而,认识大姨的人都觉得她是一个实在的好人。
大姨少女时在家里常常干的是男子汉应该干的活。担水、收麦、扬场、牵骡子碾场……繁重的农活和家务,让大姨变的成熟起来,在十六岁时她想尽快离开焦庄,把自己嫁了。后来媒人就把大姨说到了椿林的平峨村。小时候,听别人老是说平峨,我心想这个村名字叫“苹果”,村里肯定有很多的苹果,在那里肯定能吃到好多苹果。结果,此平峨非彼“苹果”,这个村不种植苹果,我在那里没吃到苹果。
嫁到平峨的大姨,住进了破旧的厦房。姨夫还在部队当兵,家里头里里外外都是大姨一个女人家在操持着。后来生了表姐、表哥,生活的担子更重了,管娃、种地,还要伺候年迈的公爹,大姨在婆家忙碌得团团转。八十年代初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关中的农村,大姨把前院的房子腾出来养鸡,在后院垒了猪圈逮了猪娃开始养猪,整日忙前忙后,只为能贴补家用。
大姨和她的二妹我的母亲感情亲近,记忆里从未见过她们红过脸,吵过架,更没有相互私底下说过对方的不是。大姨见不得她的妹妹受可怜,总是在困难的时候能伸手帮一把。为了让她的妹妹能把日子过起来,大姨和姨夫拉着架子车,走了三十多里的田间小路,把架子车上的两头猪崽,送到了焦庄我家里。我父亲那个时候在湖北工作,大姨怕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清苦,无依靠。她经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,带些吃的用的,来看我们。大姨在那个年月给了我那个曾经孤单清冷的家很多温暖的照料,这些如同深深心湖里面亮烁的珍珠,永远让人难忘。
后来姨夫转业到县公安局,大姨一家人搬到了县城。全家先是蜗居在公安局后窑的宿舍里,再到看守所的宿舍楼。八十年代末在县城北面的新安东巷盖了两层小楼的院子,大姨的居住环境才彻底稳定了下来。到了县城的大姨不愿当干部家属,吃清闲饭,依旧凭借自己的勤劳,在城里北塔底下的农贸市场摆摊卖布匹。人手不够时,就把我母亲从乡下叫来帮忙。母亲带着我来到了县城,高级的楼房,时髦的喇叭裤,让乡里的孩子新奇向往。
九十年代初,大姨在渭清路北段公路边经营了一家汽车弹簧板店铺。门店不大,但汽车配件齐全,小到灯泡,大到车梁,品类繁多,生意也比较好。那个年代正逢城乡大开发大建设时期,只要脑袋灵活,人们干啥都能挣到钱。渭清路蒲城段又是南北交通枢纽,不计其数的大货车昼夜不停在奔跑着,司机们每天都是风风火火。跑得多,挣得多,汽车也在超负荷行驶,配件损耗也大,弹簧板经常断裂需要更换。大姨的汽车配件部每天来购买弹簧板及其他配件的司机络绎不绝,生意十分的火爆。寒暑假我和表哥常常晚上住在那里看店,半夜时配件部的街门经常被大车司机砸得啪啪响,往往都是车深夜坏在公路上,急切地想让人开门买配件。
大姨见人不笑不说话。买完东西,不着急走的车户,就坐在狭小的店里聊天,大姨给他们倒水,遇到饭点会热情地递上一双筷子。很多顾客就把大姨叫婶婶,成了多年互相来往的朋友。
新安东巷的独家院住上了,姨夫又在公安局当了领导,大姨一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。来新安东巷找大姨和姨夫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求办事的、探望的、走亲戚的,院子里的人一拨接一拨。大多是从乡间来的各种各样的亲友,叫妈叫姨叫妗子叫姐的,沾亲带故的像走马灯一样,纷纷跑来围着大姨转。大姨一一承接着,没有丝毫的看不起人,没有分别心,实诚待人。因为大姨家饭食好,好多亲戚的孩子放假了也都爱去她家。孩子们一去就住下不走。暑天时,楼上楼下六间房都住满了人,整个小院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有的孩子宁愿晚上挤睡在地板上,也不愿回家。大姨爱孩子,从不嫌聒噪,每天按时按点提供着变样饭,每顿都是用大锅做饭,满满的一锅饭。
我也爱去大姨家里。不仅因为大姨家里好吃的好玩的多,也更因为那里有着宽松的生活环境。大姨很少责骂孩子们,犯了错最多只是大喊一声对方的名字。孩子们就不敢再继续造次了。我到了大姨的门店和家里,一待就是一个暑假,在那里表姐和表姐夫也比较喜欢我,凡事都照顾着我。我是独生子,性子略显孤独,他们待我就像亲弟弟一样,从不分远近,让一颗脆弱敏感的少年的心,得到了强大的呵护。
在大姨的家,我第一次读到了贾平凹很多的书,如《商州三录》《白夜》等。受到贾平凹的影响,十三岁的少年尝试着开始了所谓的日记体写作。几大本的笔记上记录了我的青春日记,也写了不少的永远发表不了的诗歌。这些都是在大姨家里完成的。后来我发现,大姨也爱看书,经常夜深了,大姨躺在床上,戴着近视镜,手棒书籍,看的专注。小学只上了三四年的大姨,通过几十年的努力,能阅读小说、会算账,彻底拥有了文化的自信和自觉。
1995年大姨把生意交给了表姐和姐夫经营。生意上的事情她不再操心,开始在家休养了。但大姨的身体却出了问题。一个秋天,二舅来到大姨家。小院的大门紧紧关闭,二舅怎么也叫不开门。无奈之下,二舅从东邻居翻墙跳进院里。进到卧室发现,大姨趴在房间桌子上一动不动。二舅紧忙把人送到医院,医生说血压高得吓人。在医院吊了几天针,大姨回到了家。几天后头又昏的厉害,口齿有点不清。大姨住进了医院,经检查诊断为脑梗。虽然得了病,但大姨生活还能自理,她坚持用运动进行康复训练,抬手、甩手、走路……日复一日地锻炼,她在心里憧憬着终有一天不灵便的腿脚会和以前一样活动自如。大姨体胖,每迈出一步要比常人吃力,她拖着沉重的步履在自己的院子里来来回回的走,向命运讨要着健康。
人和命运是一个永恒的主题,远没有胜利与失败、抗辩与妥协那样简单。在一次锻炼的过程中,大姨下门厅的台阶时不慎跌倒了,右脚骨折,人被摔得神志不清。醒来后,她的两腿开始稀软,只要一站着,人颤抖的就快要倒下去了。从那时起,大姨的身边就离不了人。起先姨夫还能形影不离的搀扶着大姨四处活动,但没过几年大姨脑梗后遗症的症状更加明显,她双腿彻底不能站立。姨夫抱不动了,家里就开始雇保姆照顾。下肢瘫痪的大姨,从此的行动,完全不由自己。任凭被别人抱起来,坐着、躺着、抱着……家里人抱不动了,就开始雇保姆照顾。
那个时候,大姨自己还可以自己端碗吃饭,但随着年迈体弱,身体的肌肉和脑神经开始萎缩。慢慢的双手也举不起来了,吃饭开始让人喂着吃。全身上下似乎只有肠胃的功能保持得比较好。依然喜欢吃羊肉泡馍、葫芦头这些硬饭。
坐起来、穿衣裤、蹬鞋、下床、上厕所、喝水、吃饭、离开客厅去院子、从院子回到客厅、从客厅再回到卧室等等这些日常生活的一个个细节的动作,大姨完全没有能力去做了。但她从不沮丧,没有任何消沉的情绪,也没有拒绝生命的迹象。大姨保持着一个女人的尊严,她有自己的喜好,她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她会嗯嗯啊啊告诉照顾她的人。她想吃什么也会表达出来。家里有客人来了,她会尽力喊着人家的名字,努力和人打招呼。甚至还会不经意间瞅一眼,看来人手里拿的是啥,有没有给她带礼物。大姨热爱生活、热爱生命,更加热爱自己。
那么久了在大姨的口里从没吐露过一个“死”字。也从来没有怨恨自己不能动了。她大大方方地活着。
到了七十一岁,大姨身体机能更加的衰落。和人交流只能仅限于在喉咙里,时而流食时而正餐,虚弱的生命几次出现重大“险情”却又神奇般地缓了过来。腊月里去看大姨,整个人虽然完全瘫痪了,但仍然要求家人把她扶起来坐着和大家在一起。一根绷带把大姨牢牢箍在轮椅上,脸色红润,气色看着很好。头发被剪短的大姨坐在院子里,暖暖的阳光照洒在温润的脸庞上,犹如一位修行数年的老尼。大家都说,没事没事。看样子大姨应该可以再继续和病魔斗争下去。
惊蛰的时令刚过去几天,大姨的身体突然变得十分危重。她的儿女们昼夜守在丧失了吞咽功能,不能进食,时不时昏睡过去的母亲的身边。我从西安赶到大姨身边,大声唤着,姨、姨……听到最喜爱的外甥的呼唤,大姨竟睁开了眼睛,喉咙里异常沉闷的在回应着。我能听出来那是大姨在答应我的声音。
正午的阳光把新安东巷子里的这座小院照得暖暖和和的,大家围坐在大姨旁边说话。表哥说,到时候在院子里搭棚,把院子整体都包起来。姐夫给表哥说,乐人最少叫八口,叫六口不合适。表姐问表哥,床板在哪?表哥说,在墙边靠着呢。我扭头一看,西墙边放一张已经准备妥当的木床板。小院里一阵沉默。寿木工厂老板这时打来电话让表哥去看棺材。二舅说,用的是黄龙山里的一等柏木,一共十块板。小院里又陷入了沉默。
思维意识的光照几乎为火星的大姨静静的坐在轮椅上,头扭在一侧,眼睛使劲看着高处,从咽喉部位发出喃喃自语的声音。大姨依然安静的顽强地在坚持着。
我们起身和表哥一起去寿木工厂看棺木。走出巷口,不知是哪一户的楼上,传出了苍劲而婉转的唱腔:
天连水 水连天 白云湿透
隐现中离却了蓬莱瀛洲只为着寻才郎万里奔走
却不知谁做了燕侣莺俦
……
关中悠扬细腻的碗碗腔是大姨最爱的戏曲。近在咫尺,她却没有能力去听、去看。走出大姨的家,县城延安路大街上繁华喧闹的气息扑面而来,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,努力奔着日子,就好像过江的鲫鱼一样,一群一群向更加宽阔的河流游去。在不远的地方大姨实在是游不动了,奔不动了。
大姨虽然是人世间的一粒微尘,但曾经全副武装,尽自己全部的力量,给这个世界奉献过劳动和智慧。病残的身躯二十三年了,一直巍巍然的证明着自己的存在。踏踏实实,从不亏欠别人的大姨,成为了一个生命的传奇。
大姨少女时在家里常常干的是男子汉应该干的活。担水、收麦、扬场、牵骡子碾场……繁重的农活和家务,让大姨变的成熟起来,在十六岁时她想尽快离开焦庄,把自己嫁了。后来媒人就把大姨说到了椿林的平峨村。小时候,听别人老是说平峨,我心想这个村名字叫“苹果”,村里肯定有很多的苹果,在那里肯定能吃到好多苹果。结果,此平峨非彼“苹果”,这个村不种植苹果,我在那里没吃到苹果。
嫁到平峨的大姨,住进了破旧的厦房。姨夫还在部队当兵,家里头里里外外都是大姨一个女人家在操持着。后来生了表姐、表哥,生活的担子更重了,管娃、种地,还要伺候年迈的公爹,大姨在婆家忙碌得团团转。八十年代初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关中的农村,大姨把前院的房子腾出来养鸡,在后院垒了猪圈逮了猪娃开始养猪,整日忙前忙后,只为能贴补家用。
大姨和她的二妹我的母亲感情亲近,记忆里从未见过她们红过脸,吵过架,更没有相互私底下说过对方的不是。大姨见不得她的妹妹受可怜,总是在困难的时候能伸手帮一把。为了让她的妹妹能把日子过起来,大姨和姨夫拉着架子车,走了三十多里的田间小路,把架子车上的两头猪崽,送到了焦庄我家里。我父亲那个时候在湖北工作,大姨怕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清苦,无依靠。她经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,带些吃的用的,来看我们。大姨在那个年月给了我那个曾经孤单清冷的家很多温暖的照料,这些如同深深心湖里面亮烁的珍珠,永远让人难忘。
后来姨夫转业到县公安局,大姨一家人搬到了县城。全家先是蜗居在公安局后窑的宿舍里,再到看守所的宿舍楼。八十年代末在县城北面的新安东巷盖了两层小楼的院子,大姨的居住环境才彻底稳定了下来。到了县城的大姨不愿当干部家属,吃清闲饭,依旧凭借自己的勤劳,在城里北塔底下的农贸市场摆摊卖布匹。人手不够时,就把我母亲从乡下叫来帮忙。母亲带着我来到了县城,高级的楼房,时髦的喇叭裤,让乡里的孩子新奇向往。
九十年代初,大姨在渭清路北段公路边经营了一家汽车弹簧板店铺。门店不大,但汽车配件齐全,小到灯泡,大到车梁,品类繁多,生意也比较好。那个年代正逢城乡大开发大建设时期,只要脑袋灵活,人们干啥都能挣到钱。渭清路蒲城段又是南北交通枢纽,不计其数的大货车昼夜不停在奔跑着,司机们每天都是风风火火。跑得多,挣得多,汽车也在超负荷行驶,配件损耗也大,弹簧板经常断裂需要更换。大姨的汽车配件部每天来购买弹簧板及其他配件的司机络绎不绝,生意十分的火爆。寒暑假我和表哥常常晚上住在那里看店,半夜时配件部的街门经常被大车司机砸得啪啪响,往往都是车深夜坏在公路上,急切地想让人开门买配件。
大姨见人不笑不说话。买完东西,不着急走的车户,就坐在狭小的店里聊天,大姨给他们倒水,遇到饭点会热情地递上一双筷子。很多顾客就把大姨叫婶婶,成了多年互相来往的朋友。
新安东巷的独家院住上了,姨夫又在公安局当了领导,大姨一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。来新安东巷找大姨和姨夫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求办事的、探望的、走亲戚的,院子里的人一拨接一拨。大多是从乡间来的各种各样的亲友,叫妈叫姨叫妗子叫姐的,沾亲带故的像走马灯一样,纷纷跑来围着大姨转。大姨一一承接着,没有丝毫的看不起人,没有分别心,实诚待人。因为大姨家饭食好,好多亲戚的孩子放假了也都爱去她家。孩子们一去就住下不走。暑天时,楼上楼下六间房都住满了人,整个小院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有的孩子宁愿晚上挤睡在地板上,也不愿回家。大姨爱孩子,从不嫌聒噪,每天按时按点提供着变样饭,每顿都是用大锅做饭,满满的一锅饭。
我也爱去大姨家里。不仅因为大姨家里好吃的好玩的多,也更因为那里有着宽松的生活环境。大姨很少责骂孩子们,犯了错最多只是大喊一声对方的名字。孩子们就不敢再继续造次了。我到了大姨的门店和家里,一待就是一个暑假,在那里表姐和表姐夫也比较喜欢我,凡事都照顾着我。我是独生子,性子略显孤独,他们待我就像亲弟弟一样,从不分远近,让一颗脆弱敏感的少年的心,得到了强大的呵护。
在大姨的家,我第一次读到了贾平凹很多的书,如《商州三录》《白夜》等。受到贾平凹的影响,十三岁的少年尝试着开始了所谓的日记体写作。几大本的笔记上记录了我的青春日记,也写了不少的永远发表不了的诗歌。这些都是在大姨家里完成的。后来我发现,大姨也爱看书,经常夜深了,大姨躺在床上,戴着近视镜,手棒书籍,看的专注。小学只上了三四年的大姨,通过几十年的努力,能阅读小说、会算账,彻底拥有了文化的自信和自觉。
1995年大姨把生意交给了表姐和姐夫经营。生意上的事情她不再操心,开始在家休养了。但大姨的身体却出了问题。一个秋天,二舅来到大姨家。小院的大门紧紧关闭,二舅怎么也叫不开门。无奈之下,二舅从东邻居翻墙跳进院里。进到卧室发现,大姨趴在房间桌子上一动不动。二舅紧忙把人送到医院,医生说血压高得吓人。在医院吊了几天针,大姨回到了家。几天后头又昏的厉害,口齿有点不清。大姨住进了医院,经检查诊断为脑梗。虽然得了病,但大姨生活还能自理,她坚持用运动进行康复训练,抬手、甩手、走路……日复一日地锻炼,她在心里憧憬着终有一天不灵便的腿脚会和以前一样活动自如。大姨体胖,每迈出一步要比常人吃力,她拖着沉重的步履在自己的院子里来来回回的走,向命运讨要着健康。
人和命运是一个永恒的主题,远没有胜利与失败、抗辩与妥协那样简单。在一次锻炼的过程中,大姨下门厅的台阶时不慎跌倒了,右脚骨折,人被摔得神志不清。醒来后,她的两腿开始稀软,只要一站着,人颤抖的就快要倒下去了。从那时起,大姨的身边就离不了人。起先姨夫还能形影不离的搀扶着大姨四处活动,但没过几年大姨脑梗后遗症的症状更加明显,她双腿彻底不能站立。姨夫抱不动了,家里就开始雇保姆照顾。下肢瘫痪的大姨,从此的行动,完全不由自己。任凭被别人抱起来,坐着、躺着、抱着……家里人抱不动了,就开始雇保姆照顾。
那个时候,大姨自己还可以自己端碗吃饭,但随着年迈体弱,身体的肌肉和脑神经开始萎缩。慢慢的双手也举不起来了,吃饭开始让人喂着吃。全身上下似乎只有肠胃的功能保持得比较好。依然喜欢吃羊肉泡馍、葫芦头这些硬饭。
坐起来、穿衣裤、蹬鞋、下床、上厕所、喝水、吃饭、离开客厅去院子、从院子回到客厅、从客厅再回到卧室等等这些日常生活的一个个细节的动作,大姨完全没有能力去做了。但她从不沮丧,没有任何消沉的情绪,也没有拒绝生命的迹象。大姨保持着一个女人的尊严,她有自己的喜好,她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她会嗯嗯啊啊告诉照顾她的人。她想吃什么也会表达出来。家里有客人来了,她会尽力喊着人家的名字,努力和人打招呼。甚至还会不经意间瞅一眼,看来人手里拿的是啥,有没有给她带礼物。大姨热爱生活、热爱生命,更加热爱自己。
那么久了在大姨的口里从没吐露过一个“死”字。也从来没有怨恨自己不能动了。她大大方方地活着。
到了七十一岁,大姨身体机能更加的衰落。和人交流只能仅限于在喉咙里,时而流食时而正餐,虚弱的生命几次出现重大“险情”却又神奇般地缓了过来。腊月里去看大姨,整个人虽然完全瘫痪了,但仍然要求家人把她扶起来坐着和大家在一起。一根绷带把大姨牢牢箍在轮椅上,脸色红润,气色看着很好。头发被剪短的大姨坐在院子里,暖暖的阳光照洒在温润的脸庞上,犹如一位修行数年的老尼。大家都说,没事没事。看样子大姨应该可以再继续和病魔斗争下去。
惊蛰的时令刚过去几天,大姨的身体突然变得十分危重。她的儿女们昼夜守在丧失了吞咽功能,不能进食,时不时昏睡过去的母亲的身边。我从西安赶到大姨身边,大声唤着,姨、姨……听到最喜爱的外甥的呼唤,大姨竟睁开了眼睛,喉咙里异常沉闷的在回应着。我能听出来那是大姨在答应我的声音。
正午的阳光把新安东巷子里的这座小院照得暖暖和和的,大家围坐在大姨旁边说话。表哥说,到时候在院子里搭棚,把院子整体都包起来。姐夫给表哥说,乐人最少叫八口,叫六口不合适。表姐问表哥,床板在哪?表哥说,在墙边靠着呢。我扭头一看,西墙边放一张已经准备妥当的木床板。小院里一阵沉默。寿木工厂老板这时打来电话让表哥去看棺材。二舅说,用的是黄龙山里的一等柏木,一共十块板。小院里又陷入了沉默。
思维意识的光照几乎为火星的大姨静静的坐在轮椅上,头扭在一侧,眼睛使劲看着高处,从咽喉部位发出喃喃自语的声音。大姨依然安静的顽强地在坚持着。
我们起身和表哥一起去寿木工厂看棺木。走出巷口,不知是哪一户的楼上,传出了苍劲而婉转的唱腔:
天连水 水连天 白云湿透
隐现中离却了蓬莱瀛洲只为着寻才郎万里奔走
却不知谁做了燕侣莺俦
……
关中悠扬细腻的碗碗腔是大姨最爱的戏曲。近在咫尺,她却没有能力去听、去看。走出大姨的家,县城延安路大街上繁华喧闹的气息扑面而来,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,努力奔着日子,就好像过江的鲫鱼一样,一群一群向更加宽阔的河流游去。在不远的地方大姨实在是游不动了,奔不动了。
大姨虽然是人世间的一粒微尘,但曾经全副武装,尽自己全部的力量,给这个世界奉献过劳动和智慧。病残的身躯二十三年了,一直巍巍然的证明着自己的存在。踏踏实实,从不亏欠别人的大姨,成为了一个生命的传奇。
发布日期:2024-04-1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