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布日期:
老屋兴起:书写寻根连根养根的情怀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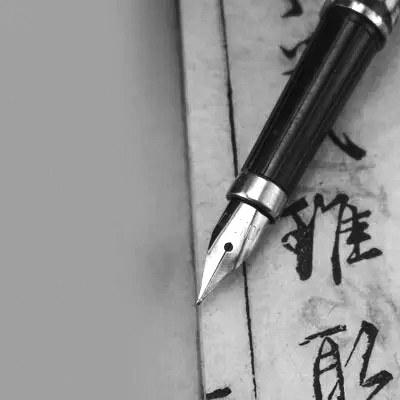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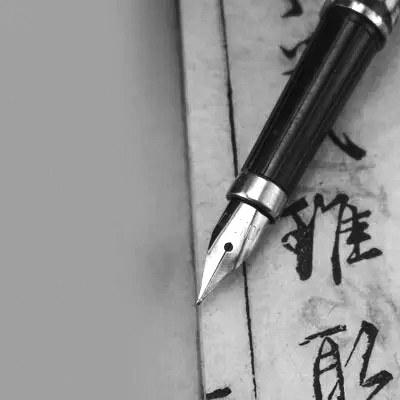
“终于写完了初稿!这是我坚持业余创作十年来,写的最快的一部作品,因为心中有太多的感触在生发,要说出——”看着刚刚打印出的厚厚一沓书稿,范作家很是感慨。
2022年12月6日,是范超文学馆在范家老屋建成两岁纪念日。范超文学馆是关中大地上首个建设在乡村之中的青年文学馆,惠泽各方,启迪后学,意义不凡,影响深远。开馆两年声誉广为人知,作用日益发挥,一切都进入有序运转阶段。在靠近两岁纪念日的某个晚上,馆长范作家的创作欲望之水喷涌而出,开始写作这部长篇文章。人到中年的他,和所有同龄人一样,身处无限焦灼抽扯之中,但他还是排除万难,利用深夜和清晨静心创新,仅用近一个月时间,顺利写出这部近20万字初稿新作。
范作家习惯性称这部作品为《老屋》,又结合当下乡村振兴语境,命之为《兴起》,待定,他说:这部书稿,实质上更是自己重构的一个“纸上范超文学馆”,向阔别三十年之故乡的又一次长篇集中回馈。
这部新作以一个决意冲出闹市缰锁回归本真田园的游子赤子“范无病”的视角,深入故地,亲近故人,看见乡村的时代变迁,看见人生的岁月更迭,看见生命的脆弱无常,看见活者的卑微坚强,那些宁静村庄里的躁动的魂灵,清素日常里跌宕的人态,有坚硬有柔软,有美丽有忧伤,有的似乎毫无踪迹有的又真切发生,是出世更是入世,是逃避更是进发,是茫然更是救赎。万千世象,寻常巷陌,五味杂陈,充满希望,是再“普通不过”又”独一无二”的乡愁,是中国版的《瓦尔登湖》和《鱼王》,是现实版的《我和我的家乡》,是我爱我的家乡的永恒咏唱。
范作家说,在时代的舞台中,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伟大的戏剧,一经开始演绎,便永远难以停下。而“范无病”离乡进城又返乡的三十年,正是中国三千年乡村史发生巨变的三十年,“范无病”和“我们”,也必将是在中国最后一代传统乡村文化中长大的人了,“我们”每天都在技术革新,社会结构,文化环境等等地巨大变化被熏陶着,“我们”坚守着承上启下的使命,然后齐步走向勃勃生机、欣欣向荣的新时代。所以范超觉得有必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,自然而然地展示出来,作为见证这个时代变迁的一个文本。
文学博士、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韩春萍是首批看到范作家书稿的评论家之一,在第一时间看完这部书稿后,她热情洋溢的写了一篇鉴赏性文字,名曰《让老屋立在文学中》,与范作家由衷与状态很是相契。文章写到:“2017年末因一次学术会议,我第一次见到范超,随后和来自云南的评论家杨荣昌跟随范超去了他的范家村。我记得我们三人站在冬日阳光下的村口说话,范超指着田地说起他的童年往事,远处是昭陵静默,近处是乡声入耳,范家村就夹杂在这两者中间。我们三人就像闯入者一般引来村人的注视,那种感觉似乎范家村既熟悉又陌生,它像所有的故乡一样正改变着模样,既让人欣喜又让人惆怅。
“范超的文字就是这复杂情感里涌出的冲动,散发出的感染力会让人不由自主被他渗透。他的文字和他的人一样,具有一种平易近人的力量,他化用的关中方言给人如聊家常的亲切感。我们那次站在范家村村口聊天的情景就像一个心灵意象,让我初探范超的精神世界和文学书写:我们不论是谈历史,谈大地,谈耕作,还是谈文学,在拉拉杂杂中,范超总能把叙事推进到他的目标上。他具有这样的兼容性和掌控力,能把身边人吸引进他的行动和叙事中。
“这部长篇小说给我同样的感受。围绕老屋翻新为文学馆的过程,主人公范无病穿梭在城乡之间,他不仅串联起了城市与乡村,还串联起了文艺界、商界与政界。想起来并无太大戏剧冲突的事件,之所以能被范超写成20万字的长篇小说,仔细读来其中依靠的是人物强烈的情结与话语的推动。全篇少见人物的直接引语式对话,基本都是通过转述人物话语推进叙事,这种写法乍看有庞杂之感,但以范超清新隽永的散文文风而论,这部小说热闹的言说声音大概是他有意为之。范超于热闹处为文,似乎每一个人的声音于他而言都是不可割舍的,他参与着,倾听着,见证着,让这些声音汇聚为一条话语的河流。这既是人物的释放又是作者的行动,是化解寻路故乡而不得之焦虑的有效方式。他在文中写道:村子在时,方向还在,老屋在时,位置还在,若都失去,谁能记得我们存在的经纬坐标?我们这一代人,要眼睁睁地看着这种失去,这种痛苦,痛彻肺腑。走进城里,我们寻找未来,在紧张的中年缝隙里,我们思念归路。但那,终究是一条难以回去的路。上面的引文道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和情结,于是范超改造老屋作为文学馆这件事就具有了某种仪式感,它牵动了众多参与者,所有人的热心汇聚在一起,指向了共同的乡愁。
“眼下的故乡就是一个老屋,如何翻新它?如何永远保有它?范超以文学之名想要保存的这个老屋,是每个离乡而不能返回的人心中永远的情结。只不过对于一般人而言,这件事稍有差池就容易让人误解。不过范超将文学馆定位在红色基因、家风传承、文化扶贫和建设上就表达了一种连根养根的情怀。连根养根是当代文化人的使命,范超的“老屋”文学馆和这部小说开启的话题打开了寻路故乡的一种可能性,也许他还会因此激发更多人的相关文学经验,让文学成为大地上新长出的庄稼。”
——抚着厚厚的一沓书稿,范作家深有感慨发自肺腑的说:文学馆建成运营不断造福家乡了,现在,20万字的书稿又初步写完将继续弘道兴文了,2022年。也就这样在劳作和收获中到了岁尾,我才觉得,让我倍尝艰难困苦的这段年月,终于没有虚度。如今我像范家村最标准的前辈农民一样,面对着劳动果实,细品一年来耕作的劳累和忻悦。写作和种地一样,靠的就是耐力和持恒,靠的就是日复一日的耕读。我就是凭着一股子种地的精神完成这两件感恩故乡的大事的。当一切如愿,一切付出也就都值得了!向前辈致敬,向乡亲致敬,向老屋致敬,向自己致敬。祝福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关心我和帮助我成长的有缘人好心人,都诸事吉祥,梦想成真!
版权所有:西北信息报社 技术支持:锦华科技
陕ICP备05010893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6100004000028
地址:西安市新城·省政府大楼7层15号 电话:029-87292915 电子邮箱:xbxxb@xbxxb.com
陕ICP备05010893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6100004000028
地址:西安市新城·省政府大楼7层15号 电话:029-87292915 电子邮箱:xbxxb@xbxxb.com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