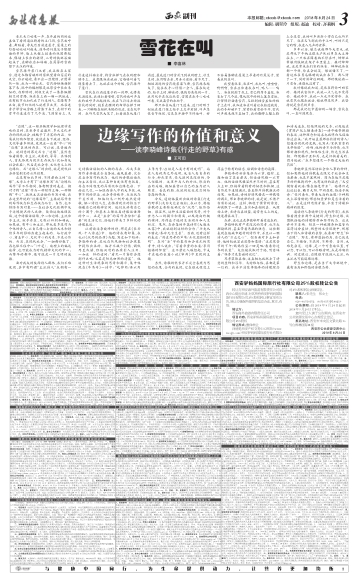发布日期:
边缘写作的价值和意义
■王可田
“边缘”,这一颇具物理学和地理学意味的名词,在竞争日益激烈、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社会,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。如果我们稍加留意,就能在当下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诸多领域,发现这一远离“中心”的“边缘”区域的存在。可以说,是普遍存在。就词意的界定而言,“边缘”,显然意味着弱势,非主流,次要的,等等。具体到人,首先体现为现实生存状态(比如身处社会底层),然后是社会学、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化。而“边缘人”的出现,就是现代社会分裂剧变的必然结果。
正是有如此多的、不同层面上的“边缘”,文学上才有了“边缘书写”或“边缘化写作”等不尽相同、各有侧重的表达。相对于将“边缘”作为一种创作立场,一种解构“中心”、挑战主流话语的书写方略,我在这里所说的“边缘写作”,主要就写作者的写作状态和生存状态而言。当然,也不排除书写对象——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边缘境况的人或物。陕西这块地理区域,这个诗歌话语场,中心和边缘、主流和非主流,似乎存在,又难以辨别和确认。如果说,有中心和主流,那也更多是作为个体的诗人,以自己精心打造的文本和持续多年的影响力建立起来的。与行政中心、商业中心、文化中心的关系,不是必然的。而且,在现代社会,“一切都四散了,再也保不住中心”(叶芝)。地理上的偏远地带,也可能成为时代精神文化的中心;而繁华的都市,很可能是一片文明的废墟。
面对庞大的陕西诗人群体,我们不难发现,其中有所谓“主流诗人”或拥有一定诗歌话语权的人物的存在。而大多数写作者分散在全省各地,遍及基层,完全是业余写作的状态。他们的诗歌话语或向主流靠近,或以某种自发性有意疏离,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质化和边缘色彩。下面这几位,一如陕西诗人中的大多数,从事不同的职业,社会身份殊异,生活状态千差万别。但他们无一例外地热爱诗歌,倾心诗性人生,在物质现实的挤压下拓展自己的精神空间。他们或许有自己的小圈子,但基本上都远离诗歌话语场的中心。正是“业余”的写作身份和“基层”的生活定位,给他们带来了多样化的诗歌表达。
以前读过李晓峰的诗,那是在《长安风·十人诗选》中。他的诗我有印象,我也以《沉思的品质》为题,写过如下短评:李晓峰的诗,是从自然风物和社会现象中提炼出来的。他并不缺少抒情、调侃乃至戏谑,但他沉思的品质引人注目。一如这样的诘问:“看见一片雾你会想到什么呢/尤其是阳光初照的清晨”。他这种对生活现象的思考和揭示,集中体现在《牛角号》一诗中:“吃掉肉/再以肉上角为号/应该是人类才有的发明”。站在人类视角之外反观、反省人类自身的行为,抑或罪恶,毫无疑问是深刻的,令人信服的。这里牛与人的对比,惨痛的血肉关联,极似基督以自己的血为世人赎罪。善良的弱,成就的往往是悲悯与崇高的伟力。
今天,通读他最新出版的诗集《行走的野草》(太白文艺出版社),我以为,将他诗歌的主要特征确定为“沉思”,依然恰切。很显然,这种生活层面的思考,对于世态人心的揭示和剥离,以及趋向终极的拷问,均得益于他的生活阅历和人生积淀。果然,在诗集的开篇诗作《大散关之雾》中,我就读到这样的金句:“历史从不借光/秦岭无言生长”。后面,还有这样的表述:“捋直思考的芦苇/点化丑陋的聪明”。在对“法”字的象形和会意式的思考中,诗人说出:“穿着华贵的衣裳/享用褴褛的仰望”。这不禁让人联想起,卡夫卡在他的长篇小说《审判》中呈现的主题。
当然,诗歌的优长并不完全表现为思想的成果,金句的表现,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特有的语感、语调和诗意的氛围。
李晓峰的新诗集分为六章,题材、主题和语言显出层次,但话语风格一以贯之。他的话语风格显然并不时新,甚至有点土旧,但携带着特有的韧性和执拗,这自然是不追随潮流,甚至排斥诗歌潮流的结果。如果说,诗的抒情风格是一种歌唱的调式,那么李晓峰的诗,就是说,不惜平白质朴地说。这样,牺牲了惯常的诗意,却获取了一种真,真实和真相的真。从理论上讲,当诗与真结盟,通常意义上的美,便退居其次了。
或许,这也正是李晓峰所着意追求的。
李晓峰既有严肃深沉的思考,也不乏揶揄讽刺,甚至带着恶搞的快感。这些都表现在他城市题材的诗作中,并且以一颗诗人的“方正之心”。但当面对乡土和亲情,他的叙说显出深挚和柔情:“这是寒食节的下午/妈妈你显一回灵吧/看看你过冬的衣裳”。大红袍花椒对于他,则意味着:“体香才是靠谱的记忆”。
思考获取真相,这真相也就脱去了诗意的虚饰和浮华。无论雅与俗,真都是第一位的。我并不清楚李晓峰的诗歌理念和诗美追求,但依照他的文本,以及他在《贫困户炕上躺着诗集》一诗中略带揶揄的表述,这种理念和追求也就明白无误地传达出来:“我开始羡慕那些热情的诗人/想植些现代的皮肤,也写点/玄机重重的生命体验”。的确,他的诗不为抒情,也不够新潮和现代,但体味生活,传达生活真相。即便揭示丑和恶,也是怀揣着美的。因为他说:“我多想遇见一个路过大地的花匠”。
李晓峰显然深谙社会和人事的种种,但如果将他的诗歌表达限定于社会和生活层面,也是不客观的。因为在他不是很多的终极拷问中,也有这样的疑虑:“天空模仿着死海/像在豁免什么”。他将目光拉远拉长,瞩目太阳,叩问屈原,给海子献诗:“你闪着电,带着大海的血腥/于神殿之上深情俯视/那些仅靠梦和灵感活着的人”。正是这种思维扩张,丰富了诗歌和精神的维度。
通读诗人李晓峰《行走的野草》,我犹豫着搜索出两个关键词:野生和边缘,试图概括他的诗歌特质和写作状态。这或许并不准确。但在一种被圈养和监管而显得过分羞怯、规整的文学环境中,观察当下诗人和诗歌的长势,我看好“野生”和“边缘”。野生,有种蓬勃的力,自己就是自己,不模仿,不混同,不附势。当然,也难免杂芜。边缘,是一个可靠地位置,可以怨,可以怒,可以冷眼旁观,或是冷嘲热讽。时过境迁,边缘很可能跃入主流,而主流也可能退居边缘。
野生和边缘,是在当下文学环境中,最有活力和价值的诗歌态势。
“边缘”,这一颇具物理学和地理学意味的名词,在竞争日益激烈、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社会,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。如果我们稍加留意,就能在当下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诸多领域,发现这一远离“中心”的“边缘”区域的存在。可以说,是普遍存在。就词意的界定而言,“边缘”,显然意味着弱势,非主流,次要的,等等。具体到人,首先体现为现实生存状态(比如身处社会底层),然后是社会学、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化。而“边缘人”的出现,就是现代社会分裂剧变的必然结果。
正是有如此多的、不同层面上的“边缘”,文学上才有了“边缘书写”或“边缘化写作”等不尽相同、各有侧重的表达。相对于将“边缘”作为一种创作立场,一种解构“中心”、挑战主流话语的书写方略,我在这里所说的“边缘写作”,主要就写作者的写作状态和生存状态而言。当然,也不排除书写对象——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边缘境况的人或物。陕西这块地理区域,这个诗歌话语场,中心和边缘、主流和非主流,似乎存在,又难以辨别和确认。如果说,有中心和主流,那也更多是作为个体的诗人,以自己精心打造的文本和持续多年的影响力建立起来的。与行政中心、商业中心、文化中心的关系,不是必然的。而且,在现代社会,“一切都四散了,再也保不住中心”(叶芝)。地理上的偏远地带,也可能成为时代精神文化的中心;而繁华的都市,很可能是一片文明的废墟。
面对庞大的陕西诗人群体,我们不难发现,其中有所谓“主流诗人”或拥有一定诗歌话语权的人物的存在。而大多数写作者分散在全省各地,遍及基层,完全是业余写作的状态。他们的诗歌话语或向主流靠近,或以某种自发性有意疏离,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质化和边缘色彩。下面这几位,一如陕西诗人中的大多数,从事不同的职业,社会身份殊异,生活状态千差万别。但他们无一例外地热爱诗歌,倾心诗性人生,在物质现实的挤压下拓展自己的精神空间。他们或许有自己的小圈子,但基本上都远离诗歌话语场的中心。正是“业余”的写作身份和“基层”的生活定位,给他们带来了多样化的诗歌表达。
以前读过李晓峰的诗,那是在《长安风·十人诗选》中。他的诗我有印象,我也以《沉思的品质》为题,写过如下短评:李晓峰的诗,是从自然风物和社会现象中提炼出来的。他并不缺少抒情、调侃乃至戏谑,但他沉思的品质引人注目。一如这样的诘问:“看见一片雾你会想到什么呢/尤其是阳光初照的清晨”。他这种对生活现象的思考和揭示,集中体现在《牛角号》一诗中:“吃掉肉/再以肉上角为号/应该是人类才有的发明”。站在人类视角之外反观、反省人类自身的行为,抑或罪恶,毫无疑问是深刻的,令人信服的。这里牛与人的对比,惨痛的血肉关联,极似基督以自己的血为世人赎罪。善良的弱,成就的往往是悲悯与崇高的伟力。
今天,通读他最新出版的诗集《行走的野草》(太白文艺出版社),我以为,将他诗歌的主要特征确定为“沉思”,依然恰切。很显然,这种生活层面的思考,对于世态人心的揭示和剥离,以及趋向终极的拷问,均得益于他的生活阅历和人生积淀。果然,在诗集的开篇诗作《大散关之雾》中,我就读到这样的金句:“历史从不借光/秦岭无言生长”。后面,还有这样的表述:“捋直思考的芦苇/点化丑陋的聪明”。在对“法”字的象形和会意式的思考中,诗人说出:“穿着华贵的衣裳/享用褴褛的仰望”。这不禁让人联想起,卡夫卡在他的长篇小说《审判》中呈现的主题。
当然,诗歌的优长并不完全表现为思想的成果,金句的表现,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特有的语感、语调和诗意的氛围。
李晓峰的新诗集分为六章,题材、主题和语言显出层次,但话语风格一以贯之。他的话语风格显然并不时新,甚至有点土旧,但携带着特有的韧性和执拗,这自然是不追随潮流,甚至排斥诗歌潮流的结果。如果说,诗的抒情风格是一种歌唱的调式,那么李晓峰的诗,就是说,不惜平白质朴地说。这样,牺牲了惯常的诗意,却获取了一种真,真实和真相的真。从理论上讲,当诗与真结盟,通常意义上的美,便退居其次了。
或许,这也正是李晓峰所着意追求的。
李晓峰既有严肃深沉的思考,也不乏揶揄讽刺,甚至带着恶搞的快感。这些都表现在他城市题材的诗作中,并且以一颗诗人的“方正之心”。但当面对乡土和亲情,他的叙说显出深挚和柔情:“这是寒食节的下午/妈妈你显一回灵吧/看看你过冬的衣裳”。大红袍花椒对于他,则意味着:“体香才是靠谱的记忆”。
思考获取真相,这真相也就脱去了诗意的虚饰和浮华。无论雅与俗,真都是第一位的。我并不清楚李晓峰的诗歌理念和诗美追求,但依照他的文本,以及他在《贫困户炕上躺着诗集》一诗中略带揶揄的表述,这种理念和追求也就明白无误地传达出来:“我开始羡慕那些热情的诗人/想植些现代的皮肤,也写点/玄机重重的生命体验”。的确,他的诗不为抒情,也不够新潮和现代,但体味生活,传达生活真相。即便揭示丑和恶,也是怀揣着美的。因为他说:“我多想遇见一个路过大地的花匠”。
李晓峰显然深谙社会和人事的种种,但如果将他的诗歌表达限定于社会和生活层面,也是不客观的。因为在他不是很多的终极拷问中,也有这样的疑虑:“天空模仿着死海/像在豁免什么”。他将目光拉远拉长,瞩目太阳,叩问屈原,给海子献诗:“你闪着电,带着大海的血腥/于神殿之上深情俯视/那些仅靠梦和灵感活着的人”。正是这种思维扩张,丰富了诗歌和精神的维度。
通读诗人李晓峰《行走的野草》,我犹豫着搜索出两个关键词:野生和边缘,试图概括他的诗歌特质和写作状态。这或许并不准确。但在一种被圈养和监管而显得过分羞怯、规整的文学环境中,观察当下诗人和诗歌的长势,我看好“野生”和“边缘”。野生,有种蓬勃的力,自己就是自己,不模仿,不混同,不附势。当然,也难免杂芜。边缘,是一个可靠地位置,可以怨,可以怒,可以冷眼旁观,或是冷嘲热讽。时过境迁,边缘很可能跃入主流,而主流也可能退居边缘。
野生和边缘,是在当下文学环境中,最有活力和价值的诗歌态势。
版权所有:西北信息报社 技术支持:锦华科技
陕ICP备05010893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6100004000028
地址:西安市新城·省政府大楼7层15号 电话:029-87292915 电子邮箱:xbxxb@xbxxb.com
陕ICP备05010893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6100004000028
地址:西安市新城·省政府大楼7层15号 电话:029-87292915 电子邮箱:xbxxb@xbxxb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