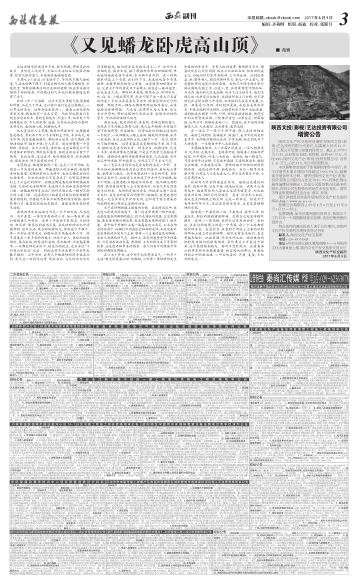发布日期:
《又见蟠龙卧虎高山顶》
去延安蟠龙卧虎湾对于我,轻车熟路,那里是我的故乡。虽然是二九时节,不似三九冻烂石头般寒冷彻骨,但寒气依旧袭人,车窗凝结着皑皑白霜。
车拐入205省道,川道狭窄了,串沟风不歇气地吹着,气温也仿佛下降了,村落边偶见的人都弓腰缩背,手装兜里,唯有公路两边的行道松树碧绿,给这萧杀凄凉增添了些许暖意,不时驶过的火车也打破寂静使这里有了生气。
我的心中一片温暖。这并不是车里暖气使周身暖和所致,而是几十年来,无以数计地行走在这条路上,一以贯之的感受。这种感受发自内心。看着山由光秃秃渐渐变绿,路由狭窄一天天变宽。而我则从骑自行车到坐长途公共车,再到坐面包车,而至小车,从华发少年到两鬓斑白,个人的荣辱、进退、悲欢与社会经历相同。这种变化,春雨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
从玉皇庙折入玉贯路,路更加明显狭窄,这条路曾经是蟠龙、贯屯和下坪三个乡镇的主干线,车水马龙,好生热闹,现在发展城镇化,都似彩云追月,鸟飞高枝,纷纷涌向城市,撤乡并镇,行人寥寥。前边好像有一个急转桥,司机说。我点头称是,告许他,这座石桥是七十年代建煤矿时修的,那时技术落后,给现在的安全留下了隐患。在此之前,过这道河,枯水期踩垫石,旺水期趟水,若发洪水,则只能望水兴叹了。
过得桥去,眼前便豁然一亮,这是一片开阔地,先前是一片茂密的庄稼。那谦虚低头的金谷穗,张扬昂首的红高梁,沉稳持重的玉米棒子,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档案里。而如今这些已不复存在了,已明显清晰地打上了工业化的烙印。公路左侧是高大雄伟的镇政府大楼、气派的采油指挥部、先进的火车站和夹杂其间的门面。公路右侧则是采油厂的停车场以及一眼望不到头的二层门面。这漂亮的门面房是村民们勒紧裤腰带集资修建的,可建起几年来不似预想的增金收银,依旧紧锁门户,落寞孤寂地站在路边。房屋过剩在农村首见端倪。
离镇四里之处从右过河是一片平坦之地,而后进沟。沟不甚宽,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,似一条长带,钮扣般缀着几个村庄。这条小河发源于卧虎湾,又经四咀、何家峁、郭家庄的泉水汇集,在我幼时的记忆中清澈甘甜、经年流淌,现在却似有似无,有些地方干涸了。第一个村庄是郭家庄,公路与村子隔着这条小河。村子座落在一里多长的阳坡上,四五十户人,虽住的比较稀疏,各自成院,但皆座北向南,风水极好,不论春夏秋冬,一天都在阳光沐浴下,按迷信的说法,这正合宜“门对青山水长流”之吉。别说这村子还真有几个在外发展不错的。上中学时,我有几个极要好的同学住在此村,我不止一次到过这里,现在在此,淡忘的记忆又变得清晰起来,他们的音容笑貌又涌上心头,油然而生亲切之感,探出车窗,拍了两张何家岇与四咀毗邻,单从地形地貌是分不清的,本为两个自然村。在一排两层底砖窑上卜壳前,我们停下车,我走近从各个角度拍照,准备带回家给老父亲看。这是国营四咀煤矿旧址,父亲七十年代曾是井下采煤工,就住在一层砖窑里,我也来过几次。那时机声轰鸣,煤堆成山,热闹非凡,吃、住、玩,小镇应有尽有,而今只留下这一排无门无窗的砖窑卜壳兀立在萋萋荒草之中,瞪着空洞而艾怨的眼晴。那院子的一棵参天槐树默默地陪伴着它,或许能给它些许慰籍。几天后,我将照片给父亲看,从父亲口中得知,那时这棵树已长在这里,我便为此树的坚贞,为此树的痴情而叹息。
再往后走,便是四咀村,原来阳、背两边都住着人,而现在只见阳坡上隐有人烟,鸡犬之声相闻,而背坡只留下残垣断壁、旧窑破院。记得从我们村翻山过来的一个院子,一线四眼或三眼土窑洞,杨姓同学结婚,我早一天来到,在这土窑洞的土炕上睡了一宵。次日,便参加了他的婚礼。记得宴客是在宽畅的院子里,院下是沟,脑畔亦是凿齐的土岸。时至今日,白驹过隙,已过30多年,详情琐事我已模糊,只是这个情景总在脑海中萦绕。遗憾的是杨同学故居虽破尚在,人已进城,孙子也已呀呀学语,俨然城里人,全然没了丁点乡土气息。
我一直弄不清闫家沟是否与卧虎湾是一个村。当年全公社抽调强壮劳力在这里打坝造田,谁知大山滑坡,竟将数人吞没。此中就有我村一后生的对象,当时他们正在热恋,从他身上我知道了什么叫悲痛欲绝,按乡下风俗,没搬酒瓶(订婚)就不算结亲。他不顾父母的力阻,执意看到对象入土方悒悒而归,而且几年之内还缓不过劲来。大坝倒是依然存在,坝地里立着一簇簇玉米杆,与斐名的梁家河坝套坝一脉相承,我想逝者的魂灵一定在冥冥之中护佑大坝,应归功于前总理朱公的退耕还林以及水土治理的功效。
车子在坝侧的路上缓缓的行驶。在我的记忆中,该是进入卧虎湾的地盘了。每一道湾里便有一两个院落,这些院落在坝两侧的坡上,但不是传统的院落,它没有围墙,甚至连木栅栏都没有,更没有高大雄伟的院门,敞开着。每个院子里都伫立着一架高大的玉米笼,玉米在阳光的反射下,从栅栏中间透出金灿灿的光泽,而住宅基本还是传统的木窗木门土窑,唯有一二立着的蓝色彩钢房,显出几分现代的气息。捡畔上,还是码着整整齐齐的柴垛,只是由原来的焦蒿、黄柏刺、玉米杆根变成了苹果树枝条,这是经济林带来的福音。农人们再不用将整个冬闲时间都耗在攒柴上。
在六七十年代,这个村子也算有些名气,一则多少也沾“蟠龙卧虎高山顶”的歌曲,二则有一李姓阴阳先生和张姓响手班子。乡里人红白喜事,都须择日而行,都喜吹吹打打热热闹闹,故名头如公社书记,但书记代表正义,而他们终归是牛鬼蛇神,上不得台面。此村还有姜、折、蔡等姓人,因自然条件恶劣,竟无一户土著人,皆是榆林那边逃荒而来的杂姓。我的几个同学每日步行翻山到蟠龙镇上学,往返30里,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。为生存,他们的父辈走南路,而为了过上好日子,他们又循父迹,或举家迁往他乡,或到城郊当上门女婿,顶不济的也出去揽工挣几个活钱,如今他们已在异乡发展、扎根。好象是79年吧,学校组织夏收,我住在姜姓同学家,半夜与他到井边排队,山缝里的水不徐不疾地滴着,滴到铁皮水桶里,叮咚,叮咚,好似在敲击铁鼓,使得空旷的山野愈发寂静,一轮皓月当空,山影茫茫,树影摇摇,山风习习,倒颇是清新沁心。想到此,我不由得感慨物是人非,人去房空,流水有意,落花无情。
在一座山下一排几十间平房,每三五间分隔成院。房面兰砖到顶,玻璃窗户,防盗门,美中不足的是时至中午,太阳依然躲的远远的,不肯光顾,较之别处多了几分寒意。一位蔡姓中年人与我叙谈。
老蔡祖籍榆林,上一辈落户卧虎湾,一家人勉强度日,吃不饱,也饿不死。至改革开放,他携妻小到城郊开饭馆,历尽艰险,终至儿女成就。说到此,他一脸喜气。可是老母年过古稀,不羡城中高楼,不喜鱿鱼海参,偏想穷乡僻壤,只爱粗茶淡饭。孝顺的他只好独自回村侍候老母。他叙述得平静,面色恬淡。我打心眼里为老蔡点赞,行孝之人必是大善之人,有才与否暂且不论,必定是有德之人。
我好奇为什么将房盖在背处。他说这是建设新农村,政府补贴,这处平缓,便选址此地。谈及半山尚有住户,他说有些村人喜欢土窑洞冬暖夏凉,加之政府虽然补贴,但终究还须投资。再者,对老年人来说,每天坐在阳坬坬上晒太阳,也是一种享受。但是对于青年和中年而言,在这里是慢性自杀,这里是禁锢精神的牢狱。
路旁有一个漂亮的小院,平房整洁,窗明几净,顶盖灰瓦,鲜红的国旗猎猎飘扬。在萧瑟之处显得格外醒目。我的心一阵温暖,我断定这是村办公室。我知道,在我们的版图上的每一个角落、每一寸土地都有组织的存在。在进村后,我看到了坝地上立着的试验田牌和山坡上的试验林牌。组织没有忘记他们,更没有抛弃他们。此地虽隅,终非化外之地。政府极力想把时代与他们的距离缩短,虽然事实上可能这个距离、这个裂缝越来越大。春风不度卧虎湾。我看着满山的苍翠树木和层层叠叠、跌宕起伏的群山,看着延伸到山外的柏油路,心中五味杂陈,矛盾、复杂,不知如何表达……
车拐入205省道,川道狭窄了,串沟风不歇气地吹着,气温也仿佛下降了,村落边偶见的人都弓腰缩背,手装兜里,唯有公路两边的行道松树碧绿,给这萧杀凄凉增添了些许暖意,不时驶过的火车也打破寂静使这里有了生气。
我的心中一片温暖。这并不是车里暖气使周身暖和所致,而是几十年来,无以数计地行走在这条路上,一以贯之的感受。这种感受发自内心。看着山由光秃秃渐渐变绿,路由狭窄一天天变宽。而我则从骑自行车到坐长途公共车,再到坐面包车,而至小车,从华发少年到两鬓斑白,个人的荣辱、进退、悲欢与社会经历相同。这种变化,春雨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
从玉皇庙折入玉贯路,路更加明显狭窄,这条路曾经是蟠龙、贯屯和下坪三个乡镇的主干线,车水马龙,好生热闹,现在发展城镇化,都似彩云追月,鸟飞高枝,纷纷涌向城市,撤乡并镇,行人寥寥。前边好像有一个急转桥,司机说。我点头称是,告许他,这座石桥是七十年代建煤矿时修的,那时技术落后,给现在的安全留下了隐患。在此之前,过这道河,枯水期踩垫石,旺水期趟水,若发洪水,则只能望水兴叹了。
过得桥去,眼前便豁然一亮,这是一片开阔地,先前是一片茂密的庄稼。那谦虚低头的金谷穗,张扬昂首的红高梁,沉稳持重的玉米棒子,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档案里。而如今这些已不复存在了,已明显清晰地打上了工业化的烙印。公路左侧是高大雄伟的镇政府大楼、气派的采油指挥部、先进的火车站和夹杂其间的门面。公路右侧则是采油厂的停车场以及一眼望不到头的二层门面。这漂亮的门面房是村民们勒紧裤腰带集资修建的,可建起几年来不似预想的增金收银,依旧紧锁门户,落寞孤寂地站在路边。房屋过剩在农村首见端倪。
离镇四里之处从右过河是一片平坦之地,而后进沟。沟不甚宽,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,似一条长带,钮扣般缀着几个村庄。这条小河发源于卧虎湾,又经四咀、何家峁、郭家庄的泉水汇集,在我幼时的记忆中清澈甘甜、经年流淌,现在却似有似无,有些地方干涸了。第一个村庄是郭家庄,公路与村子隔着这条小河。村子座落在一里多长的阳坡上,四五十户人,虽住的比较稀疏,各自成院,但皆座北向南,风水极好,不论春夏秋冬,一天都在阳光沐浴下,按迷信的说法,这正合宜“门对青山水长流”之吉。别说这村子还真有几个在外发展不错的。上中学时,我有几个极要好的同学住在此村,我不止一次到过这里,现在在此,淡忘的记忆又变得清晰起来,他们的音容笑貌又涌上心头,油然而生亲切之感,探出车窗,拍了两张何家岇与四咀毗邻,单从地形地貌是分不清的,本为两个自然村。在一排两层底砖窑上卜壳前,我们停下车,我走近从各个角度拍照,准备带回家给老父亲看。这是国营四咀煤矿旧址,父亲七十年代曾是井下采煤工,就住在一层砖窑里,我也来过几次。那时机声轰鸣,煤堆成山,热闹非凡,吃、住、玩,小镇应有尽有,而今只留下这一排无门无窗的砖窑卜壳兀立在萋萋荒草之中,瞪着空洞而艾怨的眼晴。那院子的一棵参天槐树默默地陪伴着它,或许能给它些许慰籍。几天后,我将照片给父亲看,从父亲口中得知,那时这棵树已长在这里,我便为此树的坚贞,为此树的痴情而叹息。
再往后走,便是四咀村,原来阳、背两边都住着人,而现在只见阳坡上隐有人烟,鸡犬之声相闻,而背坡只留下残垣断壁、旧窑破院。记得从我们村翻山过来的一个院子,一线四眼或三眼土窑洞,杨姓同学结婚,我早一天来到,在这土窑洞的土炕上睡了一宵。次日,便参加了他的婚礼。记得宴客是在宽畅的院子里,院下是沟,脑畔亦是凿齐的土岸。时至今日,白驹过隙,已过30多年,详情琐事我已模糊,只是这个情景总在脑海中萦绕。遗憾的是杨同学故居虽破尚在,人已进城,孙子也已呀呀学语,俨然城里人,全然没了丁点乡土气息。
我一直弄不清闫家沟是否与卧虎湾是一个村。当年全公社抽调强壮劳力在这里打坝造田,谁知大山滑坡,竟将数人吞没。此中就有我村一后生的对象,当时他们正在热恋,从他身上我知道了什么叫悲痛欲绝,按乡下风俗,没搬酒瓶(订婚)就不算结亲。他不顾父母的力阻,执意看到对象入土方悒悒而归,而且几年之内还缓不过劲来。大坝倒是依然存在,坝地里立着一簇簇玉米杆,与斐名的梁家河坝套坝一脉相承,我想逝者的魂灵一定在冥冥之中护佑大坝,应归功于前总理朱公的退耕还林以及水土治理的功效。
车子在坝侧的路上缓缓的行驶。在我的记忆中,该是进入卧虎湾的地盘了。每一道湾里便有一两个院落,这些院落在坝两侧的坡上,但不是传统的院落,它没有围墙,甚至连木栅栏都没有,更没有高大雄伟的院门,敞开着。每个院子里都伫立着一架高大的玉米笼,玉米在阳光的反射下,从栅栏中间透出金灿灿的光泽,而住宅基本还是传统的木窗木门土窑,唯有一二立着的蓝色彩钢房,显出几分现代的气息。捡畔上,还是码着整整齐齐的柴垛,只是由原来的焦蒿、黄柏刺、玉米杆根变成了苹果树枝条,这是经济林带来的福音。农人们再不用将整个冬闲时间都耗在攒柴上。
在六七十年代,这个村子也算有些名气,一则多少也沾“蟠龙卧虎高山顶”的歌曲,二则有一李姓阴阳先生和张姓响手班子。乡里人红白喜事,都须择日而行,都喜吹吹打打热热闹闹,故名头如公社书记,但书记代表正义,而他们终归是牛鬼蛇神,上不得台面。此村还有姜、折、蔡等姓人,因自然条件恶劣,竟无一户土著人,皆是榆林那边逃荒而来的杂姓。我的几个同学每日步行翻山到蟠龙镇上学,往返30里,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。为生存,他们的父辈走南路,而为了过上好日子,他们又循父迹,或举家迁往他乡,或到城郊当上门女婿,顶不济的也出去揽工挣几个活钱,如今他们已在异乡发展、扎根。好象是79年吧,学校组织夏收,我住在姜姓同学家,半夜与他到井边排队,山缝里的水不徐不疾地滴着,滴到铁皮水桶里,叮咚,叮咚,好似在敲击铁鼓,使得空旷的山野愈发寂静,一轮皓月当空,山影茫茫,树影摇摇,山风习习,倒颇是清新沁心。想到此,我不由得感慨物是人非,人去房空,流水有意,落花无情。
在一座山下一排几十间平房,每三五间分隔成院。房面兰砖到顶,玻璃窗户,防盗门,美中不足的是时至中午,太阳依然躲的远远的,不肯光顾,较之别处多了几分寒意。一位蔡姓中年人与我叙谈。
老蔡祖籍榆林,上一辈落户卧虎湾,一家人勉强度日,吃不饱,也饿不死。至改革开放,他携妻小到城郊开饭馆,历尽艰险,终至儿女成就。说到此,他一脸喜气。可是老母年过古稀,不羡城中高楼,不喜鱿鱼海参,偏想穷乡僻壤,只爱粗茶淡饭。孝顺的他只好独自回村侍候老母。他叙述得平静,面色恬淡。我打心眼里为老蔡点赞,行孝之人必是大善之人,有才与否暂且不论,必定是有德之人。
我好奇为什么将房盖在背处。他说这是建设新农村,政府补贴,这处平缓,便选址此地。谈及半山尚有住户,他说有些村人喜欢土窑洞冬暖夏凉,加之政府虽然补贴,但终究还须投资。再者,对老年人来说,每天坐在阳坬坬上晒太阳,也是一种享受。但是对于青年和中年而言,在这里是慢性自杀,这里是禁锢精神的牢狱。
路旁有一个漂亮的小院,平房整洁,窗明几净,顶盖灰瓦,鲜红的国旗猎猎飘扬。在萧瑟之处显得格外醒目。我的心一阵温暖,我断定这是村办公室。我知道,在我们的版图上的每一个角落、每一寸土地都有组织的存在。在进村后,我看到了坝地上立着的试验田牌和山坡上的试验林牌。组织没有忘记他们,更没有抛弃他们。此地虽隅,终非化外之地。政府极力想把时代与他们的距离缩短,虽然事实上可能这个距离、这个裂缝越来越大。春风不度卧虎湾。我看着满山的苍翠树木和层层叠叠、跌宕起伏的群山,看着延伸到山外的柏油路,心中五味杂陈,矛盾、复杂,不知如何表达……
版权所有:西北信息报社 技术支持:锦华科技
陕ICP备05010893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6100004000028
地址:西安市新城·省政府大楼7层15号 电话:029-87292915 电子邮箱:xbxxb@xbxxb.com
陕ICP备05010893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6100004000028
地址:西安市新城·省政府大楼7层15号 电话:029-87292915 电子邮箱:xbxxb@xbxxb.com